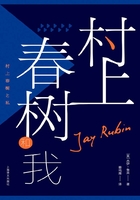
第3章 超越国境与宗教,被全世界喜爱的村上春树
邀请村上与之探讨
我和村上春树第一次见面是在1991年4月,是他参加波士顿马拉松赛的第二天。村上来到哈佛大学霍华德·希伯特(Howard Hibbett)教授的课堂,我自然也参加了。那天的主题是《再袭面包店》,当时依据我尚未发表的英译本进行了课堂讨论,那可真是相当愉快的一堂课。
《再袭面包店》写了下面的故事。
一对新婚燕尔的夫妇半夜醒来,肚子里空空如也,家中却没有食物。在他们商量要不要去通宵营业的餐馆的过程中,作为叙述者的丈夫产生了这样的念头。
我总感觉自己如今正忍受着的饥饿是一种特殊的饥饿,似乎不该在那种国道沿线的通宵餐馆随随便便敷衍了事。
所谓特殊的饥饿是怎么回事呢?
我可以将其作为一幅画面提示出来:
①乘一叶小艇漂浮在静静的海面上。②朝下一看,可以窥见海底火山的顶。③海面与那山顶之间似乎没隔很远距离,但准确距离无由得知。④这是因为海水过于透明,感觉上无法把握远近。[1]
虽然是希伯特先生的课堂,但因为将作品译成英文的是我,所以我被委以课堂讨论负责人。我向学生提问小说中的火山象征什么?于是村上不待学生回答,便当即如此断定:“火山不是象征,火山只是火山。”
我毫不气馁地高声宣布:“你们不要听他说!因为你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热烈的讨论就这样展开了。
村上的回答委实是他特有的直率,他问:“你肚子饿了会联想到火山吗?我会的。”他还继续加以说明,说他写那个短篇时正饥肠辘辘,所以就写出了火山。他可真够单纯明快的。
众所周知,村上并不希望对自己作品中出现的象征意义追根究底。岂止如此,他根本就在否定象征本身。然而一旦将作品公之于世,那部作品便不再属于他自己,而是变成读者所有,他同时也是这样一位持非常宽容、健康态度的作家。所以肚子饿的时候村上会联想到什么,对读者而言无关紧要。在《再袭面包店》里,海底火山象征着什么这一问题从早先就有许多读者讨论却一直悬而未决。然而我自负地以为与任何人相比都是对村上更为热心的读者,所以即便我断言说“这个很清楚的”,想必大家也会予以谅解吧。也就是说,这座所谓的海底火山,也许是留在潜意识中的、随时会爆发并破坏现有的平静世界的象征。
然而在村上看来,如果将火山冠之以象征,如果非要这样定义,它将失去大半的力量。他与其他作家一样,火山就是作为火山,不做任何说明,绝不妨碍每位读者在心中浮想联翩。
我想,正是这种信赖个体读者的姿态使村上春树成为被全世界阅读的作家。他把握了全世界人的心理现象——也可以说是普遍现象,并以与国界、人种和宗教全然无关的朴素且鲜明的意象表现出来。
当然,这种鲜明的意象也存在意外性。我想,这个世上肚子饿时会想象海底火山的人数量毕竟有限,也许唯此一人吧?因此,村上春树酝酿出来的意象虽说普遍、朴素、鲜明,却只能在某种程度上进行解释。那海底的火山从何而来,恐怕村上自己也搞不明白吧?
清新而又令人会心微笑、最终却不容解释的意象从村上的头脑中被直接传达给每一位读者。村上春树就像一名走私者,躲开当局的监控、溜出国境、不交关税,就这样将贵重物品从自己心里直接送到全世界读者的心中。全世界的读者或许正是渐渐感到这个叫村上春树的作家在为自己而写、理解自己心中的某种东西,所以才变成村上粉丝的吧?
所有国家的读者都在说相同的话。
“在蒙古,《寻羊冒险记》的俄语版被阅读,在乌兰巴托,人们说‘这部小说只有我们才能理解’。”[2]“说到村上春树的主人公的心理和行动,俄罗斯的年轻读者能够感同身受。”[3]韩国的金春美教授说:“对韩国的作家而言,村上春树出现的意义之一,是与和他们自己共有问题意识及苦恼的文化符号以及准确表达他们想要表达的东西的文化符号的邂逅。”[4]中国台湾的读者们说:“村上十分形象地表现了我们的感觉。”[5]
可是人的心理各不相同,难道一个作家果真能实际捕捉数百万人心中的所思所想吗?夏目漱石在《心》里,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称作“个人与生俱来的性格差异”。漱石的主人公希望用这个说法向读者解释自己自杀的动机。所以即便全世界的人并不会全部都想自杀,但也多少会感受到孤独吧?
对这一伟大的问题,村上并不故弄玄虚,而是时而笔触轻松,时而笑意融融,他总是在卖力地、并以写给读者阅读的强故事性写个不停。村上作品的主人公——包括中早期的“我”、托尼泷谷、卡夫卡、青豆、多崎作,他们都封闭在自己的思想中,将外部世界的人看作他者。村上“准确表达”的正是全世界的人每天从早到晚所经历的心情。
全世界的读者并非单纯感觉村上的作品有趣而享受阅读,而是在内心深处感动着。而且他们没有用文学性语言,而是用宗教性语言说了出来。我想,因为让数十万读者中的每个人都怀有那样的心情,所以村上才能获得如此广博的人气。
全世界读者的感受
似乎可以这样认为:既然村上被以如此多的语言阅读,那么读者当中应包含佛教教徒、基督教教徒、伊斯兰教教徒、犹太教教徒、印度教教徒、儒教教徒、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还有无数其他人。
其实无神论和不可知论不是信仰,而是表明对“宗教”这一事物的态度,所以或许应该从这个名单中排除。可实际上,正因为世界上的信仰多姿多彩,怀疑宗教的无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的立场反而才会被正当化。许多宗教自以为是地规定何为真实,但它们不可能全盘正确。反之,或许也有可能全部都是错误的。
但假如作为彼此不能共存的宗教体系的所有宗教有共通之物的话,那便是神秘性。宗教教条式地主张人生的意义,尽管缺少客观证明,却要将其意义强加于人,信徒们必须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遭遇无法解释的神秘性。
我们何以存在?宇宙何以存在?无神论者坦率承认这些无解的事物。无神论者较之宗教学家更为接受容纳我们微渺人类认为此世界绝对不可解这一感觉,而村上作品把这种不可解悉数如实接纳。
举例说明,试读一下村上发表于1985年的著名短篇小说《象的消失》,我想其目的莫不就是要让读者意识到一种无法阐明的根源性神秘?换言之,我想,《象的消失》暗示存在消失的女性和异次元世界等,这部作品就是有着诸多暗示的村上作品的缩略图。
在这篇短篇小说中,大象和饲养员一起从笼子里莫名不知所踪。大象一直在那里待到了某一天,却在翌日消失。话者如此述说。
“套在象脚上的铁环依然上着锁剩在那里,看来大象是整个地把脚拔了出去。”[6]铁环和沉重的锁连在一起,那把锁被固定在混凝土墩儿上。“象舍与‘象广场’围了三米多高的坚固栅栏。”[7]如此,即便象从铁环中拔出脚,纵身跃过栅栏,“松软的沙土路面上也没有留下任何类似象脚印的痕迹”。[8]
叙述者是自称为“我”的电器公司广告部一名孤独的职员。“我”确信大象并非从象舍中逃离,而是消失。不过他认为无法这样子说服警察和自治体。他所知道的是,和象一起,魔术也从他“敷衍的”人生及城镇的日常中消失了。
象是巨大的神秘化身,可是叙述者又说道:“人们对于自己镇上曾拥有一头大象这点似乎都已忘得一干二净。”神秘感消失之后,孤独的人只剩下买东卖西的日常生活。通过嘲讽地描述神秘性从话者的生活中消失,村上将本该深入思考的悬而未决的神秘留给了读者。无论长篇还是短篇、内容深刻或是喜剧化题材,几乎他所有的作品都将悬而未决的神秘留给了读者。
毋庸置疑,无论笔调如何轻松,或是使用多么朴素鲜明的意象进行表述,孤独依旧是孤独,日积月累以致自杀的可能性总是存在。走到自杀程度的孤独在村上永远的畅销书《挪威的森林》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也并非偶然。结果全世界的人阅读村上作品的感触便是:“啊,原来感觉如此孤独的人并非只有我一个。”当发掘到和他人共有孤独,读者反而被治愈了。
四方田犬彦教授在随笔《如何看待春树热》中做了如下论述:
“无论在什么社会,其情形都是这样的,‘村上作品群’首先作为人们治愈自己的政治性挫折、恋爱观、孤独与虚无的文本被接受,然后人们才会重新发现作者是日本人,自己手中这本书原来是翻译作品。”[9]
尽管村上作品中写了许多的自杀、死亡与悲伤,但活下去并努力获得新的体验、新的知识和新的爱这样积极的人生态度才是作者(读者)的立场,所以村上春树得到了全世界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