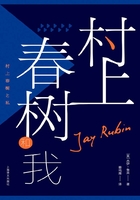
第6章 闭上眼翻译就难以为继
寻找准确表述的语句
读过《奇鸟行状录》第1部第13章《间宫中尉的长话·2》中下面这段话,我想大概没有读者不感到恶心难受。
士兵们用手和膝按住山本的身体,军官用刀小心翼翼地剥皮。他果真像剥桃子皮那样剥山本的皮。我无法直视。我闭上眼睛。而一闭眼,蒙古兵便用枪托打我的屁股,一直打到我睁开。但睁眼也罢闭眼也罢,怎么都要听见山本的呻吟。开始他百般忍耐,后来开始惨叫。[21]
这里只不过是描写蒙古将校一点一点活剥日本间谍的皮的开头部分而已,接下来残酷的画面持续了很长篇幅。翻译这段话、将惨绝人寰的日语替换成同等程度惨绝人寰的英语的那些日子至今依然历历在目。
与间宫中尉这位第13章中的叙述人不同,我不被允许哪怕有闭上眼一秒钟的奢侈。偶尔去看充满暴力的电影时,看着周围的观众闭上眼睛,我便会想起翻译那段剥皮场景的经历。有时我想和村上本人谈谈这一章,但他根本不想谈及这个话题。他说因为太残酷,会令人呕吐。
不过,作家本人只消写下这一章即可,必须进行翻译的我却不得不忍受比他漫长得多的过程。当然,我并非在说翻译某个文本比写作它更需要专注力。
自不待言,原作者需要整体想象塞满每个角落的细节,而要说翻译是最强烈的阅读方式也不算言过其实。以上述剥皮场景为例,如果读者恶心到无法忍耐,便可眯上眼或者跳读,还可以不读,但翻译的时候如果闭上眼睛,那个士兵便会用枪托不停地殴打译者,直到他睁眼为止。
翻译文学,不是单单被动地理解原著书上写的内容,译者还要积极地想象作家塞入的所有细节,也就是所有的视觉心象、声音、气味、感触、味道,寻找能用本国语言中尽可能准确表述的语句。
如果是技术性资料,不用考虑内容的机械性翻译或许可行,但文学不能那样进行。说文学翻译上所需的时间大多数情况要长于原作者也并不为过。特别是碰到血腥的场面,坐到电脑前往往都会感到痛苦。性描写场面有时也会有另一种意义上的痛苦。翻译令人欢喜的文章时,那一天也会变得愉快。
翻译芥川龙之介的《忠义》这一类时代物语的经历惊悚刺激。因为他的文体特别难,所以读者通常花20分钟就能读完的短篇会一连几日盘旋在我的头脑中,给我一种观赏武士电影般的意趣。
我翻译日本小说已有45年之久,可能是因为把大脑用在这种缓慢推进的细致操作和同时要调动大脑兴奋的过程中之故,脑髓的神经线连接似乎大为改变。将日语改写为英语时,因为要从日语原作中榨出最后一滴“果汁”,所以感觉只用自己的母语读文学有点意犹未尽。
我的日语能力无论如何都难以匹敌我的英语能力,所以颇闹了点笑话。我的英语阅读速度算是比较慢的,但再怎么全神贯注逐一仔细欣赏英语文本中的意象,也还是没有翻译时细细品味日语文本的速度来得更慢。而仅用英语阅读,因不需努力将文本替换成不同的语言,也会感觉失落。
那种探索将文本转换成不同语言的方法的努力才是翻译中的大半乐趣。特别是处理词汇、音声、措辞、句子结构诸方面极端不同的英语与日语时,译者如不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发明家,便不能将原作的神韵与意向充分传达给读者。或许将发明称为翻译全过程中的醍醐之味也不过分。我绝非想说译者就是创造者。我的意思是,莫如说是解释者更为贴切,但也有成为发明家的时候。
名词的单复数之别
村上作品的读者或许认为,在像他这样主要受美国影响的现代作家的作品中,译者可能存在发明的余地。自不待言,村上作品中有诸多爵士乐、摇滚音乐或美国作家登场,文章结构与遣词本身也有许多明显的英语化,因此他的文体经常被形容为“黄油味儿”。
翻译村上小说《1Q84》BOOK1与BOOK2时,他的文体依然带“黄油味儿”,同时还必须着力应对始终折磨着以日语为对象语的译者的各种问题,也就是说,还必须着力应对从15世纪的能乐舞台一直到涉及《源氏物语》的叙述问题。
举一个简单的具体问题,日语中无名词的单复数之分,村上像使用日语单词一样使用英语单词时,问题就会变得复杂。就连与雷蒙德·卡佛、约翰·欧文、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等作家渊源深厚的村上都没有明确区分单复数。
例如村上关于爵士乐音乐家的两册随笔集《ボートレイト·イン·ジャズ》(《爵士乐群英谱》)刊发时,一如一众其他作品,村上给加了英语副标题“Portrait in Jazz”。我想,这样做,封皮会比单纯的日语题目更酷。如果要把这本书译成英语,题目必须要改成表示文中爵士乐音乐家的肖像画的复数的“Portraits in Jazz”。村上原题目中的“ボートレイト”(中文为“肖像画”、英语为“Portrait”)被作为日语使用时既可用作复数也可用作单数,这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1Q84》中被认为是超自然存在的“リトル·ピープル”(中文为“小小人”、英语为“Little People”)成群登场。当他们作为一个集体做同一动作时没有任何问题,可是他们中的一人作为个人说话或行动时,翻译问题就出现了。例如:
“你给我们办了件好事。”声音低的小小人说。
要将这里译成英文,就必须在“声音低的小小人”后面加上下面的表达,才能传达出“小小人中的一人”(One of the Little People)这一微妙差异。
You did us a favor,says one of the Little People with a small voice.(2:403/tr.P.535/UK 566)(“你给我们办了件好事。”其中一个小小人压低声音说。)
《1Q84》中的某个人物确信天空上有两轮月亮。一轮是平时的黄色大月亮,另外一轮是偏小偏绿色、扭曲了的月亮。看见两轮月亮的人当然想要询问别人是否也能看得见,却又担心被人看作脑子出了毛病,犹豫着要不要确证这一事实。因此,两轮月亮就成了疏离感,也就是不可能对他人敞开心扉倾诉的疏离感的象征。
在日语中,登场人物谈到月亮时可以不必明确看见的是一个月亮还是两个月亮。有段名叫青豆的女人对名叫天吾的男人不挑明理由却提醒他留意月亮的简短对话。接下来,天吾在和青豆的通话中突然说了句“今天的月亮很美”,吓了青豆一跳。而下面的几行话因这种语言单复数的模糊性得以成立:
“今晚的月亮很美。”
青豆在电话话筒边微微皱眉,问:“为什么突然说起月亮?”
“我也偶尔会聊聊月亮的嘛。”
“当然。”青豆说。不过你可不是那种没有任何必要,却在电话里谈风花雪月的人。
天吾在电话一端沉默片刻,开口说道:“上次你在电话里提起月亮,还记得吧?自那以后不知怎么,月亮就在我脑中挥之不去了。于是刚才我看了下天空,澄澈无云,月亮很美。”
那么有几个月亮呢——青豆差点脱口问道,却又忍住了。这太危险。[22]
我最后把这里的“月亮”替换为“moon-viewing”,省略掉“月亮”一词,以解决单复数问题。
[Tamarn said,]“It's a nice night for moon-viewing.”[月亮→赏月]
Aomame frowned slightly into the phone.“Where did that come from all of a sudden?”[省略“月亮”]
“Even I am not unconscious of natural beauty,I'll have you know.”[省略“月亮”]
“No,of course not,” Aomame said.But you're not the type to discuss poetic subject matter(风花雪月)on the phone without some particular necessity,either.
After another short silence at his end,Tamaru said,“You're the one who brought up moon-viewing[月亮→赏月]the last time we talked on the phone,remember?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it[月亮→it=赏月]ever since,especially when I looked up at the sky a little while ago and it[省略‘月亮’;it=天空或整体状态]was so clear-not a cloud anywhere.”
Aomame was on the verge of asking him how many moons[复数]he had seen in that clear sky,but she stopped herself. It was too fraught with danger.(tr.P.343/UK 365)
与古典典故出处相关联的另一翻译问题点在于这场关于月亮的对话中英语斜体字部分的暗示。如村上所有的小说一样,这部小说中也有很多内在独白。英语中多通过使用斜体字、利用打字技术就能简单进行暗示,但如爱德华·福勒(Edward Fowler)在1992年出版的研究专著《忏悔的修辞》(The Rhetoric of Confession)中缜密证明的那样,内在独白与外在独白的区别、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的话语区别在日语中都是非常含糊的。正是因为这种含糊性,谣曲的话语方式才得以成立。
在能乐中,登场人物能够叙说自己的台词或讲解自己的行为,因此,在《船弁庆》中,出演义经的演员一直在说着自己的台词,却突然跳转到旁白的话:“那时候义经纹丝不乱。”而接下来地谣[23]又从他那里接过旁白的话,接着讲述义经的行动:“那时候义经纹丝不乱,拔出了兵器。”即便如此,也不会感到丝毫不可思议。
明治时代的小说家泉镜花(1873—1939)对能乐的舞台语言造诣深厚,他的陈述语气在登场人物的头脑中进进出出,很难正确翻译。
但是,就算在《1Q84》这样的现代小说里,也有在不求助于区分标点符号或者大小写等打字技术的情况下,出其不意地在登场人物的第一人称“我”到第三人称“他”之间进进出出的长段落。我有好多次问村上这里该用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他的回答必定是“你看着办吧”。
我觉得“看着办”一词最终道出了译者工作的全部。翻译工作就是用自己的语言、用自己认为适当的手法,尽可能地让读者体味到最接近原文的文学经验。当然,没有人知道在客观意义上“能做到”什么。最为关键的原因在于翻译是建立在译者的主观体验之上。
那么,文学翻译者的作用是什么呢?大概就是从原文本中撷取最大限度的喜悦,与读者分享想象上的经验吧。这个过程对于翻译家来说是极为主观的。然而,不正是通过它,成千上万的读者才得以一窥用它以外的办法无法触及的世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