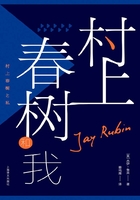
第7章 被无意识与偶然创造的“象之长旅”
伯恩鲍姆的英译
村上作品今天在全世界范围内被阅读,他在本国被认为是文体高妙的作家,然而,村上自身写下的语言丝毫无法传达给阅读被译成外语的作品的读者们。说它理所当然自是理所当然,我想,讽刺的是,以语言为生命的人(即小说家)若是希望在日本以外被阅读,便必须十分依赖他人(即译者)的语言。如果翻译的文体不佳,原作的文体无论如何高妙,也无法在国外被阅读。
在这个意义上,村上作品的国际人气要很大程度上仰仗阿尔弗雷德·伯恩鲍姆先生的翻译。最初吸引英语圈读者兴趣的就是伯恩鲍姆先生《寻羊冒险记》的灵动翻译。之后,《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和《舞!舞!舞!》都被译成活灵活现的英文,村上春树的人气益发高涨开来。
若不是美国出版社通过伯恩鲍姆先生的英译对村上作品产生了兴趣,或许我永远都不会读村上作品。正如本书开篇所述,我第一次读村上作品是在1989年夏天,起因是来自犹豫要不要推出《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翻译的美国佳酿(Vintage)出版社的拜托,出版社希望问问能读日语原文的人这本小说是否值得翻译。
我力劝应该翻译,但佳酿出版社当时还是决定不推出(现在他们已出版了村上全部作品的平装本)。当时伯恩鲍姆先生已经翻译了村上全部的长篇小说,短篇翻译尚少,所以我获准许可翻译其他短篇,开始译《象的消失》、《再袭面包店》和《眠》等作品。
后来,遇到喜欢的作品想翻译,我习惯直接拜托村上,而不可思议的是,我从未收到过“这个伯恩鲍姆先生译过了”的回答(《托尼泷谷》)。据村上说,伯恩鲍姆先生也从未遭遇“这个鲁宾已经译过了”的回答。这就证明,尽管我们二人都是村上作品狂热的读者,志向却完全不同。不过这个话题并未就此落定。
当时,美国的一流出版社科诺普出版社提出出版村上的短篇集,伯恩鲍姆先生和我的译稿均被寄送过去,编辑分别选定伯恩鲍姆先生译的9篇和鲁宾译的8篇(二人原稿当然完全没有重复)。
书终于问世了,报纸和杂志上开始出现书评,评论家们无一例外地或者只谈及伯恩鲍姆先生的译作或者只提到我的,没有人两方均涉及。这无疑也在无意识中反映了两位译者的志向差异。
而《象的消失》(使用The Elephant Vanishes中的同名短篇为题)这一短篇集的编纂过程中,我经常被询问和伯恩鲍姆先生分别承担了哪些工作,但我只能回答编辑加里·菲斯凯特约翰根本没有与译者商量,完全根据自己的喜好编成。
《象的消失》最终被编纂成这种形式,原因无他,而是许多人的品味与偶然,也就是在无意识的力量下完成的。我想,在这两种意义上,这都是好事。
现在还活着的作家的文学很难存在“定评”,因此,学者兼译者无论多么希望从这位作家的作品群整体印象出发进行判断,断定某一作品的意义及重要性,选择能永世流传的作品进行翻译,因其作品群自身始终在发生变化,所以与其说他依赖的是客观判断,莫如说是依赖个人主观喜恶、亦即自己的品位。这很可怕,同时也很刺激。
自己花很长时间费尽心血翻译的东西或许半年时间就无人读了,而且在后世看来,或许还会被嘲笑明显漏掉了名篇,选择了劣作。然而,翻译活着的文学,也可以让自己无限参与到自己连续无意识和偶然的创作过程中去,可以品味到这一独特的刺激。
“井”的意象
翻译村上小说的工作中,我越来越感觉无意识和偶然格外重要。从成名作《且听风吟》起,村上文学中开始频繁出现走廊与井的意象,承担着现实世界通向无意识世界通道的作用。作品中的人物希望通过这一通道进入自己人性的内核,或者反过来,完全被遗忘的记忆通过通道猛然再现,停留在极度不可思议的现实性上。
在我1997年完成的英译本《奇鸟行状录》中,主人公冈田亨长时间待在井中,探索自己的记忆和无意识世界。这本由3部构成的长篇小说的第2部第5至11章中,主人公始终坐在井底。他在井中从第89页待到了第181页,将近100页中除了思考什么也没做。第3部的高潮场景也在井中上演。
村上建议我考虑翻译《奇鸟行状录》时,第1部尚在月刊杂志《新潮》上连载,还属于根据作品群的整体印象无法判明作品重要性和意义的阶段(也就是作家自身大概也不清楚小说大部分内容会是怎样的阶段),而我必须回答“Yes”还是“No”。我欣然答应“Yes”,开启了3年之久的持续冒险。作为学者,我虽然同时也写作家评论,但作为译者,这种经历越发让我对文学的无意识力量心怀敬意。
英译短篇集《象的消失》1993年出版,从此村上的象开启了国际性长旅。2003年6月4日,坐在世田谷大众剧场的我为象之旅——这一超越时间、超越语言、跨越两片海域、超越文化,然后又返回原点的旅行错愕不已。
村上的小说《象的消失》1985年在东京出版,1991年我在波士顿翻译它,同年11月18日在杂志《纽约客》上登载,1993年和村上其他16篇短篇合起来,由前面说的科诺普出版社以The Elephant Vanishes[24]为题在纽约出版。必定是1993年至2003年的某一天,英国表演艺术家西蒙·迈克伯尼(Simon McBurney)用英语朗读了《象的消失》。后来,他和日本演员们将17篇短篇中的3篇,用迈克伯尼既不可能阅读也不可能理解的村上自己的语言搬上了舞台。
结果,它成为一部大胆、现代,且运用多媒体技术的作品,我由衷感觉它忠实到令人吃惊地表现了村上原作中的现代都市精神,同时也汲取了日本传统艺能——能乐的特色。
若非英国人迈克伯尼担任《象与罚》这一舞台剧主要的创造性指导,只怕我未必会对作品中看到的传统艺能要素如此惊讶。日本的传统艺能与其说是拟态化,不如说它是建立在物语、舞蹈和歌唱之上的表演,是将文本在视觉和听觉上表象化。在歌舞伎中,这种表象既有国际感又有绚烂华丽感。在能乐美学中重视最小化,舞蹈也停留在简素抽象层面,拟态的动作仅是将舞蹈格式化的延长,同时文本的咏唱又成为这一切的基石。
相似的美学也可以在《象与罚》中找到。与其说《象与罚》进行了拟态化的描述,莫如说它将村上的语言想象性地格式化,而且仅表现为最小限度的视觉和声音。舞台的成果接近观众作为读者各自的个人体验,而在观众席上我们又能够进行共享。村上曾经说过:“能和情感与共的人尽情谈论喜欢的书,是人生最大的喜悦之一。”[25]
当我们思索村上笔下的象之长旅时,《象与罚》带来的共通的“喜悦”益发显著。
象之长旅至此依然没有结束。2005年3月,当村上在海外的业绩跋山涉水来到日本时,新潮社刊发了最初以英语版问世的短篇集The Elephant Vanishes值得纪念的日语版《象的消失》。封皮上称赞道:
“纽约选出的村上春树初期短篇17篇,以与英文版相同的作品构成回馈读者。”
通过这一反向引进,1985年启程的象终于回到了本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