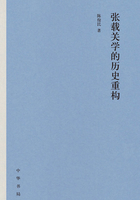
一、开启关学研究正当性的被质疑
简要地说,先是宋明理学会议上据《简报》称,我的关学研究“脱离了马克思主义指导”;接着,在我没有出席的多次关学及相关的学术会议上,都会听到尖锐的批评声,问题症结,还是攸关我所主张的“关学不是一般‘关中之学’,而是‘关中理学’”、“关学不只是一个张载思想,它同理学思潮相联系,共始终,也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史”等观点是否能以成立,即由我开启的关学研究是否具有正当性。批评者甚至在署名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下卷这样严肃的学术专著中,加入批判文字,指责我关于明代关学集大成者吕柟、冯从吾“上承张载,下开李颙”的思想传承关系,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是“强行拼凑在一起的”。更为甚者,是书竟然使用如下的语言批评说:
所谓“关学”的始作俑者冯从吾,他所汇编的《关学编》,原不过是地志的性质,一如《金华丛书》、《江西丛书》、《岳麓丛书》之类。而李元春、张骥却从中牵率为承前启后的“宗传”关系,真可谓是好事者为之,殆无意义。(2)
此段文字原为是书第五章中《薛瑄的学传——“关中之学”》一小节的结语。按标题来说,这一小节其内容似乎是要通过薛瑄《读书录》等文本和吕柟《文集》、《经说》、语录等原典,论述两者之间“学传”授受的内在思想联系,可是,无论过去和现在,令我和我指导作吕柟、韩邦奇、冯从吾思想研究的海内外数位博士生及学界友人都感到特别遗憾的是,本节的主要内容,却是利用《明儒学案》转述的二手材料,重点宣示明代关中无关学的论断。为此,竟不顾学术专业最基本的规则,将《学案》原史料中的“关学”一词,统统引述为“关中之学”,仅仅不到五页文字,至少出现三处引述史料失实的硬伤;而且以“始作俑者”、“强行拼凑”诸词语,把首立“关学”之名、始为“关学”作学术定位的冯从吾《关学编》,以及王心敬、李元春、贺瑞麟等清代关中学者先后递补增订的《关学续编》,说成是“好事者为之,殆无意义”。
更令我至今仍不得其解的是,《关学编》本是经冯从吾亲手编定、按陕毕懋康初刻、冯从吾次子冯嘉年增修的二十二卷本《冯少墟集》中的二十一至二十二卷,可是,是书却说:“原不过是地志的性质。”学界共知,所谓“地志”者,地方志也。退一步说,即就是将《关学编》硬归入“地志”之类,那么,按地志学专家章学诚“志乃史体”的“史法”规定,它无疑应是必含“三家之学”的史学范畴,但不知是书持之何据,又将它比附为《金华丛书》和《中国丛书综录》著录的所谓《江西丛书》、《岳麓丛书》之类?这显然是指“郡邑丛书”,史称“丛书”之名,盛于明清两代,第一部郡邑丛书《盐邑志林》刊行年代,至少在晚于《关学编》十多年之后的天启年间。所谓“丛书”者,乃依一定原则与体例而汇集各种或同类,或不同类,或多类性质的重要著作为一专集之大部头书也。如果说,按照“经史子集”四部编辑刊行的《金华丛书》,一如依据“正、续、外”三编汇集的《西京清麓丛书》之类,还近于同类性质可比的话,那么,以《关学编》比附任何“郡邑丛书”,都是风马牛不相及也。这种在严肃的学术大著中随意引述史料、混淆文献类别的行文方式,如此批评指责,实际是没有任何学术价值的。所以,自《关学源流辨析》正式发表之后的十五六年里,我没有作任何学术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