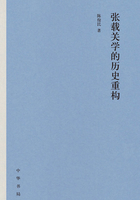
二、“以仁心说,以学心听”
然而,值得回味的是,在1986至1997的十年间,我清理校点的首批关学典籍《关学编(附续编)》、《蓝田吕氏遗著辑校》和《二曲集》被中华书局列入《理学丛书》先后出版之同时,我的几部专著《张载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派》、《吕大临易学发微》、《中国哲学研究论集》和《关中三李年谱》也由人民出版社、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台湾学生书局、台湾商务印书馆、台湾允晨文化公司先后向全球发行,尤其是我协助指导德国慕尼黑大学东方研究所郎宓榭(Michael Lackner)、傅敏怡(Michael Friedrich)等博士主持翻译的世界第一个张载《正蒙》德文译本,也由著名的麦那(Meiner)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关学研究已受到海内外学界友人的关注。中华书局《书品》编辑部约我撰写了《关学研究与古籍整理》一文,随后,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通讯》1998年第一期“研究动态”栏目,又刊载了台湾关学研究学者吴有能博士的《陈俊民教授与关学论争》长篇报道,这一论争,才被正式公布于世。但对我来说,当看到这些研究、整理作品面世,正如《书品》拙文所说:
最勾起我回顾的还是,我如何从关学及宋明理学的研究转向理学典籍整理的问题。据说,这也是学界不少关心我的朋友们很想知道的一段学术经历。无论在当时还是以后,也可以说一直至今,我所思考的都不是该作什么“答辩”,而是如何能让《关学编》、《冯少墟集》、《二曲集》,以及至今还流落在海外的那些明代地方理学《宗传》类的珍本,尽快点校整理出版,先使学人能读到该读的书,才能谈到学术研究,自然也就会避免上述大著那些不该出现的失误。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才非常感慨地曾对“关学研究室”我的同事与研究生说:古籍整理要比编写几本通史更重要,只有投身于古籍整理工作,才能真正使“学术以天下为公器”,看不到古籍,何谈学术?(《书品》1987年第1期)
这便是我有生以来唯一的一次回应批评者时所说出的学术初衷,它决定了我后半生的学术信仰和走向。
但对于海内外宋明理学和关学研究者来说,真正学术意义上的“论争”才刚刚开始。以下将会涉及到的诸如“关学是有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还是所谓“明清实学思潮主流推动关学走向了复兴”?张载哲学定位究竟以“气本论”为是,还是以所谓“太虚本体论新说”为是?等等争论,一直延续未止。更为有趣而令人欣慰的是,据说昔日坚持“北宋亡后关学渐归衰熄”、“明清无关学”的专家及其后学,也开始整理研究张载以后的“关学典籍”了。这种非常有趣的学术现象,无非一则表明关学自身具有存在、传续的生命力;二则表明我开启的关学研究亦非无本之谈,其实是对关中传统哲学思想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它自身充满生机,是具有生命力的学术创作活动。其中曲直得失,或昔非今是,或昔是今非,乃不足为奇,当淡定以平常心处之。这正是对我一贯奉行“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辨”(《荀子·正名》语)之学术原则的最好验证。不过,我还时常告诫我的海内外弟子:在学术上,与其以公心辩,实不如先“不争不辩,让历史告诉未来!”
(1) 参见刘学智:《“关学洛学化”辨析》,《中国哲学史》2016年第3期,第62—69页。
(2) 侯外庐等:《宋明理学史》下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