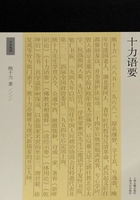
与某报
经书难读,不独名物训诂之难而已。名物训诂一切清楚,可以谓之通经乎?此犹不必相干也。此话要说便长,吾不愿多说,亦不必多说,只述吾少年读《诗经》之一故事。
我在少年读《诗经》之先,已经读过四书,当然不甚了解,但是当读《诗经》时,便晓得把孔子论《诗》的话来印证。《论语》记孔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我在《关雎章》中,仔细玩索这个义味,却是玩不出来。《论语》又记夫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我那时似是用《诗义折中》作读本,虽把朱子《诗传》中许多以为淫奔的说法多改正了,然而还有硬是淫奔之诗不能变改朱子底说法的。除淫奔以外,还有许多发抒忿恨心情的诗。变雅中许多讥刺政治社会昏乱之诗,其怨恨至深。如《巷伯》之忿谗人,曰“投畀豺虎,豺虎不食”云云。昔人言恶恶如《巷伯》,谓其恨之深也。夫谗贼之徒固可恨,然恨之之情过深,恐亦失中和而近于邪。《论语》又记子谓伯鱼:“汝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欤?”朱注:正墙面而立者,一物无所见,一步不能行。易言之,即是不能生活下去的样子。人而不为二《南》,何故便至如此?我苦思这个道理,总不知夫子是怎生见地。朱注也不足以开我胸次,我又闷极了。总之,我当时除遵注疏通其可通底训诂而外,于《诗经》得不到何种意境,就想借助孔子底话来印证,无奈又不能了解孔子底意思。
到后来,自己稍有长进,仿佛自己胸际有一点物事的时候,又常把上述孔子底话来深深体会,乃若有契悟。我才体会到孔子是有如大造生意一般的丰富生活。所以读《关雎》,便感得乐不淫哀不伤的意味。生活力不充实的人,其中失守而情易荡,何缘领略得诗人乐不淫哀不伤的情怀?凡了解人家,无形中还是依据自家所有的以为推故。至于“思无邪”的说法,缘他见到宇宙本来是真实的,人生本来是至善的,虽然人生有很多不善的行为,却须知不善是无根的,是无损于善的本性的,如浮云无根,毕竟无碍于太虚。吾夫子从他天理烂熟的理蕴去读诗,所以不论他是二《南》之和、《商颂》之肃以及《雅》之怨、《郑》之淫、《唐》之啬、《秦》之悍等等,夫子却一概见为无邪思。元来三百篇都是人生的自然表现,贞淫美刺的各方面称情流露,不参一毫矫揉造作,合而观之,毕竟见得人生本来清净。夫子这等理境,真令我欲赞叹而无从。宋儒似不在大处理会,反说甚么善的诗可以劝,恶的诗可以惩,这种意思已不免狭隘。朽腐即是神奇,贪嗔痴即是菩提,识此理趣,许你读《三百篇》去。
再说人而不为《周南》《召南》,何故便成面墙?我三十以后渐渐识得这个意思,却也无从说明。这个意思的丰富与渊微,在我是无法形容的。向秀《庄子注》所谓“彰声而声遗,不彰声而声全”,就是我这般滋味。如果要我强说一句,我只好还引夫子底话: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这话意义广大精微。孔子哲学底根本主张,就可如此探索得来。他确是受过二《南》的影响。话虽如此,但非对孔子底整个思想有甚深了解的人,毕竟不堪识此意味。我又可引陶诗一句略示一点意思,就是“即事多所欣”。试读《葛覃》《芣苜》《兔罝》诸诗,潜心玩味,便见他在日常生活里,自有一种欣悦、和适、勤勉、温柔、敦厚、庄敬、日强等等的意趣,这便是“即事多所欣”。缘此,见他现前具足,用不着起什么恐怖,也不须幻想什么天国。我们读二《南》,可以识得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大步走上人生的坦途,直前努力,再不至面墙了。这是孔子所启示于我的。
孔子论《诗》,是千古无两。唯孔子才能以他底理境去融会三百篇《诗》底理境;唯三百篇《诗》是具有理境的诗,才能引发孔子底理境。这两方面底条件缺一不行。
我想我个人前后读《诗经》和《论语》的经验,我深信读经之难,不仅在名物训诂。训诂弄清了,还不配说懂得经,这是我殷勤郑重向时贤申明的苦心。
关于中学生应否读经的问题,此亦难说。吾意教者实难其人。假设有好教员,四书未尝不可选读。如我所知,杭州私立清波中学经裘冲曼、袁心灿、蔡禹泽、张立民诸君选授四书,于学生身心很有补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