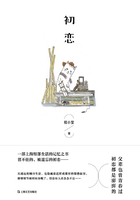
第5章
同样是饭的气味的,是海宁路的一家帆布厂飘出来的味道。也有白色的热乎乎的蒸汽。因为饭与饭单的关系,使我感觉,饭与帆布,也似乎有了联系。后来我发现,所有发“Fan”的音,都会与“饭”有关。“犯”错误,到家里便会被大人骂“夜饭不许吃”;看一本连环画正扎劲的辰光,被喊着要吃饭了,会觉得“烦”;姓“范”的人,大多胃口好,比如后来有个叫“范志毅”的男人,踢足球的,饭量肯定是大的;那时还有一个叫“范文同”的,是越南总理,一个在广播里听熟的名字,听上去不知为什么,会与一个不大好的词儿联想起来——“饭桶”。儿时诸如此类的联想,没什么褒贬之意,都是一些孩童式的胡思乱想,与孩童有限的经历与视野有关,激发最初的语感。
那时候我开始认字。我对汉字的形象化理解,几乎都类似于这样的“饭”“饭单”“帆布”“饭桶”“犯错误”“烦”的种种联想。比如“瓜”,发音的时候,嘴型是一个咧嘴啃西瓜的样子,似乎还有口水和汁水从嘴边淌下来;“哭”的音调和发音的表情,已经是一副哭相了;“笑”字,你盯着看,就像是个笑嘻嘻的面孔;“友谊”的“谊”,总归和黏乎乎粘在一起,腻滋疙瘩,比如“鲜血凝成的友谊”,感觉就像鼻屎一样可以搓成嘀溜滚圆的;“骨干”,便与骨头相关,干巴巴地撑着,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被老师封为班级“骨干”,我便开始消瘦下去,像骨干了;我的脸上泛着一些白色的斑痕,我无端会将这个“斑”与“班级”联系起来,因为班级里的男孩大多脸上会有斑痕。
也喜欢啃指甲,经常叫肚子疼,说我们的肚子里有蛔虫,我是承认的,我到现在都觉得,蛔虫都是生长在1960年代的男孩肚子里的,今天可能已经绝种,所以现在的男孩便没了“宝塔糖”可吃。吃“宝塔糖”可以解馋,但比较麻烦的是,过后我们要注意自己的大便,蛔虫是从便中排出的。这使我们在大便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忐忑。早春的时候,我们每天在学校里还要滴一种黄绿色的药水,从鼻子里滴进去,从鼻腔流到喉咙口,是水果的味道,那是预防脑膜炎的。“点滴”的词儿便是这样来的,三点水、四点水,一滴一滴,形状便是笔画里的“点”,水滴落下来的时候,形成流线形,是在空中减小阻力的形状,“点点滴滴”的词儿便很具象,到处在滴滴答答。后来,京剧样板戏《红灯记》里有句台词:“点点滴滴在心头”,我便会联想到滴鼻头的黄绿色药水和水果香味。
有一天,语文老师在上课的时候,讲到读书,用了“啃书本”的字眼,我问老师,为什么要“啃”?老师答,“啃”,就是用牙齿慢慢地咬,然后吃下肚子,对读书,就要这样,把书本知识一点一点咬下来,吃进去。语文老师的这一番话,影响我的一生。我从此看书的时候,都要吃东西,在那时,我会弄只生山芋啃,弄只冷馒头啃,后来啃压缩饼干,啃大饼,啃冷的羌饼,到现在,只要与读书有关,或者要看大部头的书,我还保留着这边读边啃东西的习惯,啃苹果,啃生梨,啃生胡萝卜。只有这样,书才能读进去。
这是我和城市以及它的细部生活的生死攸关的初恋。我的脑子里充满印象。
北站有一座高楼,14层,上海铁路局,一个轴对称的建筑,是横向的,结实得犹如搭积木时用了大量的方块相叠。那上面开着许多神秘的窗户,夜晚,里面透出日光灯白皙的亮光。大人在工作。很安静的,和外面的嘈杂分割开来。这是我对“上班”的最初印象,要上这个楼,在一个班头上,停下来,做一些每天要做的事情。我从容地在外面打量着这大楼。在那时,我要堂而皇之地进入这样的大楼几乎是不可能的。我期盼着战争爆发。我可以端着冲锋枪,一路突进去。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儿,便是登上最高处,占领上海铁路局。“突破”与“占领”的词儿,便开始在我心底里形成某种最初的男人欲念。那便是要站在一个顶点。我当然从来没有想过,我占领铁路局后要干什么。我只是觉得,我出生于此,竟从未上过这个高楼,这无论如何是不对的。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我跟着几个同学,冒充“红卫兵”,混进了这幢大楼,一口气登上顶楼,就为了从一个高处看看城市。
我趴在窗口往下看的时候,感觉是一片宁静;我的下身有一阵刺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