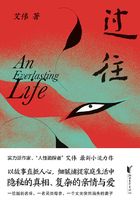
第2章
虽然每晚回家都已是凌晨,秋生还是每天早上九点钟准时到公司。办公室在“锦瑟年华”娱乐城的顶楼。这是娱乐城最安静的时刻,要到下午才会有一些客人来这儿唱歌或跳舞。当然高潮还是晚上,人们身体里的激情似乎到了晚上才蠢蠢欲动,好像夜晚对人们而言自带荷尔蒙,引导人们去追逐音乐、美酒或女人。有时候秋生想,要是没有夜晚这世界该有多么单调。
即便在办公室里秋生也喜欢戴着墨镜。他穿着衬衣,衬衫领子雪白挺括,板寸头让那两只招风耳朵更为显眼。保镖进来说,夏生在楼下有事找他。秋生皱了皱眉头。已有好久没见到弟弟夏生了,一年或者更久?记不得了。他们兄弟之间不来往很久了。秋生让保镖去把夏生带上来。
夏生站在秋生面前,面容苍白,显得有点拘谨。夏生知道秋生讨厌他是一名戏子。夏生在永城越剧团做演员,扮小生,混迹在一堆女演员中,身上一点男子气魄都没有了。秋生有一次对他出言不逊,说他最恨的一件事就是男人娘娘腔。秋生感到奇了个怪了,同父同母所生,他们兄弟俩完全是两种人。
夏生热爱演戏,舞台让他快乐。夏生对秋生的看法不以为然。秋生总喜欢把自己那套人生逻辑强加到他身上。秋生是错的。人生哪里可以如此单一,秋生也不是人生模板(事实上他也不配成为模板)。夏生自有夏生的活法。每次秋生像一位父亲一样训斥夏生时,夏生都是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有一次,秋生甚至要夏生辞了剧团的公职,到他的公司来做艺术总监。“你在这儿随便混混都比演戏强,现在谁还看你们的戏?”秋生说。自那以后,夏生不再愿意见秋生。秋生偶尔会给他打电话,问他近况,夏生都说很好。夏生知道秋生关心他,只是夏生反感秋生的关心里暗藏着一个父亲的角色。
一个星期之前,夏生收到母亲的来信。母亲在信里说她得了重病。她没有详述自己得了什么病,只说自己弥留在世的时间不多,想在最后的时光同秋生和夏生生活在一起。母亲在信里没有提起冬好。这也算正常,冬好的状况在与不在没什么区别了。夏生收到信后心情复杂。母亲是她那一代最出色的戏曲演员。越剧演员无论小生旦角还是老生小丑,基本上清一色由女性出演,夏生作为一个男生成为这个剧种的一员,不能不说是受到母亲的影响。虽然夏生和母亲在同一个圈子里,见面的次数却不多。母亲晚年嫁了一个老干部,去了北京。据说老干部是她的戏迷。母亲定居北京后,夏生没去过她的家,母亲也不太和子女联络(不过没去北京前母亲也很少联系他们)。有几次夏生进京演出,请母亲看戏,母亲和秋生一个德性,看戏后没一句好话,挑的全是毛病。“你都演成什么样子!你的才华及不上秋生的小指头。”母亲说这话让夏生既生气又委屈。秋生五大三粗,对戏根本不感兴趣,母亲竟拿他同秋生比。夏生从来没见识过秋生有任何戏曲才华,没听秋生唱过一句戏。不过母亲一直偏爱秋生,偏爱到不讲常理。夏生也就见怪不怪了。后来夏生能不见母亲就不见。夏生偶尔会想起母亲,她在忙些什么呢?在北京过得好吗?不过也只是一个念头而已,转瞬即逝。那日突然收到母亲的信,夏生还是蛮吃惊的。
夏生坐在秋生大办公桌对面,低着头,一副丧气样。他能感受到墨镜背后秋生的目光。夏生不想先开口,等着秋生说话。兄弟俩沉默了好长一阵子。秋生问:“碰到麻烦了?”夏生摇了摇头。秋生松了一口气,说:“那就好。”
秋生问起庄凌凌:“还同那个姓庄的女人搞在一起?”夏生没回答。夏生怕出乱子。秋生几年前派人警告过庄凌凌,要庄凌凌放过夏生。秋生传话给庄凌凌,说庄凌凌是都可以当夏生妈的人,难道要耽误夏生一辈子。夏生对秋生的做派一向不以为然,即便是对他的关心,也过于粗暴。秋生振振有词,说你得有自己的生活。
夏生不想同秋生多拉家常。每次都是这样,聊到后来都是一个结果——不欢而散。好像他们彼此有仇似的。从前不是这样的,小时候秋生从母亲那里偷了钱,在街头买雪糕,总是不忘给夏生买一块最好的,然后到处找夏生,找到夏生时雪糕都融化了。秋生打他一记后脑勺,说,你快吃掉,否则我不给你吃了。说着自己咽一口口水。夏生乖巧地让秋生吃一口,秋生凶狠地白他眼,不再理他。
夏生从口袋里掏出母亲的信,递给秋生。秋生很快扫了一眼母亲的信,轻蔑地说:“你就为这事来的?她也给我写过信,我没理她,我警告你,你也别理她。”
夏生直视秋生。秋生的反应他是料得到的。“她快要死了呀。”夏生说。“鬼才信她,她嘴里没一句真话。”秋生说。似乎语气还不够强烈,秋生又说:“她要死了才想起我们来?早先呢?早先她只知道一个人找乐子,这辈子像没见过男人似的。”夏生低下头,秋生的说法他无法反驳。母亲这辈子有几次婚姻?五次还是六次?多得让夏生记不过来了。
夏生今天是硬着头皮来找秋生的。这事拖了一周了。母亲信里写得很清楚,她现在一个人生活,感到很孤单。母亲难道又离开了那老干部?不管怎么样,她快死了,做儿子的不能不管她。他希望秋生能把母亲接来,秋生家大,又有保姆,可以照顾母亲。
秋生把那封信还给夏生。他转了话题,问:“你那新戏排得怎样了?”夏生很吃惊。他没想到秋生关心起他的戏来。秋生一向以夏生是演员为耻的,他不知道秋生这是何意。
一个月前,庄凌凌弄来一个剧本,非常棒。夏生也没多想秋生何以知道此事,秋生总有办法知道他想知道的,他长着一对奇怪的耳朵,好像他的耳朵在整个永城飞,没有什么事瞒得了他。夏生说:“还没排呢,钱还没找到。现在排戏就是把钱倒水里,本都收不回来,没人愿意赞助。”秋生讥讽道:“你们是把自己砸到了水里,你们一心想淹死,没人能救得了你们,早上岸早超生。”秋生还是老调调。
夏生再一次认定,和秋生谈戏就是鸡同鸭讲,自取其辱,千万不要涉及这个领域。夏生打算早些离开。他站起来准备告辞。秋生一动不动。他又打开抽屉,像在找什么。夏生本来打算走的,以为秋生改了主意,站着看秋生。秋生抬起头来说:“我警告你,你不要把她接来,你要是接来,我饶不了你。”
夏生刚升起的希望一下子破灭。他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低下了头,转身往办公室外走。他明白所谓的“饶不了你”的意思,就是秋生会揍他一顿。夏生从小没少挨秋生的揍,对他好也揍,教训他也揍。夏生往外走时,听到背后传来秋生的声音:“如果你把她接回来,我也会把她赶走的。”夏生心里冷笑了一下,想,秋生管不了他,他完全可以自己做主。他决定把母亲接回来。
夏生走后,秋生颓然倒在沙发上。一会儿,他站起来,突然唱起戏来,尖细的曲调轻柔地从他嘴中出来,和他的形象形成奇怪的反差。好像这会儿他穿上了水袖戏服,成了舞台上的花旦,兰花指翘着,身段妖娆。这些戏都是秋生小时候在黑暗的剧场看着演员们排练学的。不过秋生从来没在任何人前展示过他的“才艺”。那时候母亲到哪里都喜欢带着秋生。剧团排练时,秋生在黑暗的剧院里钻来钻去。有时候去化妆间,天热的时候,那些女人几乎袒胸露乳。她们喜欢把秋生叫成干儿子。母亲不愿意她们这么叫,她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他差点要了我的命,生他时我难产,不许你们当他的干娘。母亲越是这么说,那些女人越要占秋生的便宜。
那时候他们一家还是团聚的。母亲的演戏事业是这个家庭的中心。父亲是永城文化馆的一位音乐老师,可他的心思都在母亲身上。他正在根据母亲的演艺特长编写一出新戏,希望此剧能挖掘母亲的所有优点。很多人认为父亲不谙世道,行为怪异。秋生也信不过父亲,不认为父亲能写出好看的戏来。只有母亲崇拜并相信父亲,他们很恩爱,甚至在兄妹三人前亲热。“他们是一对活宝。”秋生对妹妹冬好说。但冬好觉得很好,很浪漫。秋生说,浪漫个屁,是不要脸。母亲在永城声名大噪后,父亲建议母亲去省城发展。“永城对你来说太小了。”父亲对母亲说。父亲渴望母亲更大的成功,好像父亲这辈子的事业就是让母亲成名成家。母亲后来真的去了省城。父亲和母亲过起了两地分居的生活。一个男人愿意牺牲自己成全一个女人,虽然疯狂,也是一种美德。母亲去省城时,带走了秋生。
秋生唱完一段戏,屏住呼吸,稳定了一下情绪。他来到垃圾筒前,找一个星期前丢弃在那儿的母亲的来信。信居然还在。他拿了回来,摊开皱成一团的信,看起来。母亲给他的信,言辞和给夏生的完全不一样。在给夏生的信里,母亲对自己来永城显得理所当然,好像回到永城和他们生活是她应有的权利。不过在给秋生的信里,母亲是可怜巴巴的,几乎在乞求秋生收留她,母亲还表达了对秋生的想念。“你是我用命换来的。”一周以前,秋生看到这句话相当反感,这句话他听太多遍,在母亲那里就是一句顺口溜,他不相信里面有什么真情实感。秋生把信折好,放到写字台抽屉里。
保镖敲门后,悄然进来。保镖也是他工作中的助手。秋生想起来了,今天需要去处理一下娱乐城的事。不久前,消防突然来到“锦瑟年华”娱乐城,找出一堆问题,下面的人搞不定。他起身,来到大楼下。坐到车上后,他改了主意,同司机说,去广济巷。司机不明所以,掉转车头,向广济巷开去。半个小时后,小车驰入那条著名的由香樟树冠交叉而成的绿色通道,蓝山咖啡馆深绿色的门面一闪而过,咖啡馆的橱窗里放着做好的糕点和一幅巨大的话剧海报。蓝山咖啡馆的主人特别小资,喜欢各种戏剧,是标准的文艺青年。秋生让司机在蓝山咖啡馆前停下。保镖先下车打开车门。秋生出来后,没像往常那样让保镖跟着。他让他们在原地等。
永城越剧团在剧院后庭的一个院子里。就是夏生的单位。秋生怕见到熟人,从院子右侧一小道拐入,那儿有一个窗子,可以进入剧院内。凭着童年的记忆,秋生顺利进入剧院。没有演出的剧院黑暗一片,因为空气不流通,秋生被一股浑浊的霉味呛到了,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他习惯性地看了看二楼,看管剧院的老头总是在二楼出现。他熟悉这个剧场的每一个角落,舞台后演员的化妆间,更衣室,剧场一楼和二楼中间的小小的电影放映室,虽然几年前剧院做了大的改造,但整体格局没多少变化。
秋生在最后一排坐下。现在他的目光适应了黑暗,剧场内的椅子和走道在黑暗中浮现出来。他默然坐着。他连自己都不清楚为什么来到这儿。他问自己,假设夏生接母亲回来(他断定夏生会这么干),他见不见她?
舞台上突然出现一对男女。两人是从幕后钻出来的,迅速黏在一起。舞台空旷,这对男女看起来很小。秋生看到这一切,很厌恶。这引起了秋生不快的回忆。母亲带着秋生来到省城,先是寄居在母亲同门姐妹家,后来省越剧团分给她一间宿舍。母亲在那个时候,背着父亲和一个男人好上了。
秋生下定决心,如果母亲到来,他绝不见她。他悄悄从剧院的前门退出去。在剧场的大厅,他找到电箱,把电闸合上。他知道这会儿,剧场里灯光闪亮,那对赤裸的男女一定惊慌失措。秋生穿过二楼的一个出口,这儿有一个铁梯,可以通往刚才进来的窗口。
秋生给孙少波打了个电话。孙少波是红酒商,娱乐城的红酒都是孙少波提供的。这阵子永城流行喝红酒。红酒生意利润高得惊人,秋生方方面面帮过孙少波不少忙。秋生到蓝山咖啡馆门口,保镖就出来打开车门。秋生竖起食指,向他摇了摇,然后走进咖啡馆。保镖迅速关了车门,严肃地站在咖啡馆门前。蓝山咖啡馆的电视机正在播体育新闻,但只出画面,听不到声音。电视机是新装上去的,奥运会不久将开幕,到时候有很多年轻人会聚到这儿来看比赛。六月奥运火炬在永城传递,秋生无意中看到了直播,夏生竟然是火炬手。秋生心里有所触动。一个人不管干哪一行,要干到夏生这份上也算不容易了。成为一名奥运火炬手无疑代表着对夏生戏曲生涯的认可。不过秋生依旧认为演戏不是什么好职业,这个职业经常会毁掉正常的人生。他们家就是个现成的标本。
保镖看到孙总急匆匆朝这边走来。孙总老远向保镖打招呼。保镖问孙总怎么来的。孙总说,车停在剧场门口,这巷子不太好停车。保镖点点头,拉开咖啡馆的小门,让孙总进去。孙少波一眼看见坐在角落里的秋生。
孙少波在秋生对面坐下,脸上下意识露出谄媚之色。秋生替孙少波要了一扎啤酒,说:“这里的黑啤不错,德国进口的,没掺水。”孙少波听了有点刺耳。有一次他被人告就是因为拉菲里掺水。其实不是掺水,是掺了同一个酒庄出产的红酒。秋生说:“我小时就在这一带玩,现在这儿没人认得我了。”孙少波不知如何接口。他知道秋生不是和他来怀旧的。他喝了一大口啤酒。刚才跑得快,确实有点口渴了。
好一会儿,秋生终于说正事。秋生说:“帮个忙可以吗?钱我会出的,你出个面就行。”孙少波很快就明白秋生的意思了。秋生想让孙少波出面赞助一笔钱给永城越剧团排一出新戏。孙少波没有理由不答应。秋生说:“剧团就在那边,看见了吗?”孙少波说:“原来这么有名的剧团在这个角落,我平时都没注意过。”秋生给了孙少波一张名片,说:“你找他,是剧团团长。等会儿打电话给他吧。”秋生想了想又说:“不要装得像施舍的样子,就说你从小喜欢唱戏,特别崇拜演员,现在有了点闲钱,想投资艺术,实现心愿。”说完秋生把服务生招了过来,结了账。孙少波要抢着结。秋生说:“你少来,我拜托你办事,当然我来,再说这能花几个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