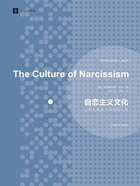
对独处主义的批判:理查德·桑内特论公共人的没落
虽然理查德·桑内特坚持认为“自恋主义正是强烈的自爱的对立面”,从而使他对自恋主义的批判比舒尔的批判更为细致、深刻,但是他也使个人领域经历了类似的贬值。在桑内特看来,那些曾经约束过大庭广众之下人们非个人关系的习俗正是西方文化传统中的精华。这些被现代人谴责为束缚人的、虚假的、置感情自发性于死地的传统曾经在人们之间建起了文明的界线,确定了在公众前表露感情的限度,发展了世界主义,并提高了文明程度。在18世纪的伦敦和巴黎,是否善于社交并不取决于人与人关系亲密。“在公园里或街道上相遇的陌生人可以毫无窘态地交谈。”他们之间有着为公众所共有的信号,这使不同阶层的人能进行文明的交谈并能合作完成公共项目,而不至于感到非得暴露他们内心深处的秘密不可。然而到了19世纪,缄默的空气被打破了,人们开始相信公共活动可以暴露行动者的内在人格。对真诚和真实的富有浪漫性的狂热追求撕下了人们过去曾在公共场合中戴上的面具,熔蚀了人们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的界限。一旦公共世界已开始被视为是自我的镜子,人们便失去了保持一定距离以及轻松幽默的人际关系的能力,因为后者是以与自我隔开一定距离为先决条件的。
桑内特认为,人们的社会关系由于在我们时代被视为自我启示的一种形式而变得异常严肃。交谈带上了自白的特点。阶级意识退化了;人们认为他们的社会地位是他们个人能力的一种反应,并为自己受到的不公正而责怪自己。政治堕落成了为达到自我实现而不是为了社会变革而从事的斗争。当自我与周围世界之间的界线崩溃后,曾经充斥政治活动各个阶段的对个人利益的开明的追求也变得不可能了。以前典型的政治人都知道如何来获取而不是如何来产生欲望(桑内特认为这是心理成熟的标志)。他像判断日常生活情况似的判断政治,看看“其中自己是否有利可图,而不是看看其中到底能不能找到自己”。然而自恋主义者却“把自我利益放在一边”,并处于欲望的极度兴奋状态之中。
桑内特的论述非常复杂并具有启发性,远非一个简单的概括所能说明。关于在游戏中和在对现实的戏剧性的重建中与自我保持一定距离的重要性,关于对自我的追求在政治领域中的投射,关于亲密人际关系的思想所带来的有害影响,他都可以给我们很多教诲。
但是桑内特关于政治取决于开明的个人利益以及对个人与阶级利益的精打细算的观点,却不能很好地解释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关系中所惯有的非理性因素。他过于忽视有财有势阶级用道德原则来为自己优越地位辩护的能力,正是这些道德原则使人们对他们进行的抵抗不仅成为对国家的犯罪,而且也成了对整个人类的犯罪。统治阶级总是试图使被统治者带着犯罪感来体验剥削与物质财富的剥夺,但与此同时他们却自欺欺人地以为他们自己的利益与全人类的利益是互相吻合的。桑内特把成功的自我实现等同于“获取而不仅止于向往”的能力,这似乎在说不做自恋主义者的唯一途径就是做个贪婪者。我们暂且不管他说的这一切是否正确,现在的事实是人们还从未绝对清楚地认识到他们的利益所在,因而在整个历史过程中他们总是倾向于把自身中的非理性因素引入政治领域中去。把现代政治中的非理性因素归罪于自恋主义、寻求人与人之间亲密关系的思想意识或“个性的文化”,不仅夸大了意识形态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而且也低估了以往时代里政治的非理性特征。
桑内特关于适当的政治应当追求个人利益的观点与托克维尔的多元论传统是一脉相承的,桑内特观念中的意识形态成分显然来源于前者。这种分析倾向于把资产阶级自由美化成唯一文明的政治生活形式,把资产阶级“文明”美化成唯一不曾腐化的社交谈话形式。从多元论的观点来看,人们所公认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瑕疵不是由政治手段就能消除的,因为政治生活本身就被看成是一个有着内在缺陷的不完善的领域。所以当人们要求从根本上改变政治制度时,他们实际上是在把个人忧虑引入政治的范畴中去。这样一来,自由主义就把自己说成是政治理性所能达到的最远限度,而把包括整个革命传统在内的超越自由主义的任何企图都斥为自恋主义的政治。桑内特所采用的托克维尔的思想方法使他无法分清60年代后期被美国文化中许多非理性因素腐化了的激进政治与很多正确的激进目标之间的区别。他的那一套分析方法使所有的激进主义以及所有想创立一个不是基于人剥削人之上的社会的政治形式都不由自主地变得可疑了。尽管他把从前的社交生活理想化,但桑内特的书却也参加了时下厌恶政治——即反对用政治手段来改革社会——的大合唱。
再者,桑内特在急于重新把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分开的同时,却忽视了这两者其实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总是互相渗透的这一事实。年轻人的社会化使政治在个人体验的层次上又处于统治地位。在我们自己这个时代,有组织的统治力量已经如此广泛地侵入了私人生活,以致私人生活几乎已不复存在。桑内特倒置因果,把当代的弊病都归咎于建立亲密人际关系的思想意识对公共生活的侵入。对桑内特、马林和舒尔来说,当前人们对自我发现、心理成长和亲密的人际关系的沉溺代表着不健康的自我陶醉和浪漫主义的泛滥。其实,对亲密人际关系的狂热并非起源于对性格的强调而是起源于性格的崩溃。今天的诗人与小说家写作并非为了赞美自我,而是为了记述自我的解体。为医治瓦解的自我而设计的心理治疗法也传递了同样的讯息。我们这个社会非但没有牺牲社会生活以促进私人生活,相反已使深情而持久的友谊,爱情和婚姻都越来越难以实现。随着社会生活越来越紧张与野蛮,那表面上能使人摆脱这些情形的个人之间的关系也带上了战争的特点。一些新治疗法用“自信果敢”和“力争恋爱与婚姻的公平”等美好字眼来为这场战争开脱,另一些治疗法把这种程式下的不持久的恋情誉为“开放式婚姻”和“开放式承诺”。就这样,他们表面上要治愈这种疾病,实际上却使它严重起来。然而他们之所以能这么做,其社会根源并非是通过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社会问题转向个人问题,从真实的问题转向虚假的问题,而是通过模糊人们痛苦——而不是那种沾沾自喜的自我陶醉。人们备受这种痛苦的折磨,却把它误认为纯粹是个人的、私下的问题。
(1) 皮埃尔·加莱特·德·马里佛(1688—1763),法国剧作家、小说家。他的剧本主要是讽刺剧和爱情喜剧。他的两部小说《玛丽安娜的一生》(1731—1734)和《暴发户》(1735—1736)对中产阶级人物作了深刻的心理研究。马里佛的代表作为1730年完成的《侍从之爱》(Love in Livery)。——译者
(2) 唐纳德·巴赛尔摩(1931—1989),美国当代作家,著有《白雪公主》短篇小说集,《回来吧,卡利加里博士》(1970),《苦痛》(小说集),《负疚的快乐》(1974)等。长篇小说有《逝去的父亲》(1975)和《业余爱好者》(1976)。1972年获美国文学艺术研究会奖。为美国作家协会及笔会成员。——译者
(3) 约翰·凯奇(1912—1992),美国作曲家。1952年他创作了4分33秒的《时间关系》——一部完全沉寂的作品。1951年创作的模糊或即兴作品《音乐的转换》取材于中国《易经》。《水上行》(1959),《剧院作品》(1960)为视听作品,可供一至八名舞蹈者、音乐演奏者或演员表演。——译者
(4) 法兰克·科穆德写道:“终结感……是我们所谓现代主义所固有的特点……总的来说,我们似乎往往把一种社会堕落的观念——这种观念由对早期马克思的新兴趣所推动,而且也为从未如此流行过的异化概念所证实——与一种技术乌托邦主义结合起来。在我们对未来的思考的方式中有着一些矛盾之处,如果我们对它们进行公开探讨,就会导致我们意图将它们加以相互补充。然而这些矛盾往往是根深蒂固的。”苏珊·桑塔格在指出“人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接受他们注定灭亡的消息”时,把以往时代对世界末日的幻想与今天对世界末日的幻想作了比较。从前对世界末日的期望往往构成了“一个对社会进行激进反叛的时刻”,然而在我们时代,这种幻想只能激起“一种不甚强烈的反应”,人们能“并无大惊小怪地”接受这种对末日的期望。
(5) 伍迪·艾伦(1935—〓),美国演员、剧作家。导演和爵士乐演奏家。他在表演时善用美国口语、土语来活泼剧情。演过戏剧《别喝水》(1966),拍过电影《谁是新猫咪》。自己创作、导演并领衔主演了《拿了钱就跑》。——译者
(6) 豪根的著作反映了当前人们对“单纯的政治途径”的失望之感(“革命所能完成的只是更换一下对弊端的管理而已”),同时也反映了桑塔格认为我们时代所特有的在灾难面前的无能为力。豪根一开始就宣告说:“事情简单得无以复加。一切都在崩溃,而你却毫无办法。让微笑成为你的保护伞。”
(7) 沃尔夫举了以下例子来说明把自我看成是“一个巨大生理潮流的一个部分”的观点的批判而出现的新的心理倾向: 一个染发剂的广告宣称:“要是我只能活一次,就让我当一个金发女郎!”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8) 早在1857年,布朗逊就用与20世纪批判家们的批判所类似的言辞批判了现代生活不断分化的个人主义倾向。“我认为由引起了一个批判与革命的时代的基督教改革运动所开始的摧毁工作已经走得足够远了。一切可以被瓦解的都已被瓦解,一切可以被摧毁的也已被摧毁,现在已经是进行重建工作——即调和与友爱的工作——的时代了……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结束我们对过去的敌视。”
(9) 超自我这一社会在个人意识中的代理人总是由对父母以及其他权威象征的内化了的代表所组成,然而我们应该把来自古老的、俄狄浦斯时期以前的印象的代表与那些基于更后期的印象,因而反映了对父母力量的更现实估计的代表区别开来。严格说来,那些后期的代表帮助构成了“自我理想”——即对别人对我们的期望以及我们在他们身上所热爱的特点的内化;而超自我与自我理想不同,它起源于结合了侵略与愤怒的幻想,起源于父母对满足孩子一切本能需要的必然的无能为力。然而超自我中侵犯性的、惩罚性的,甚至是自我毁灭的部分往往被后来的体验所修改,这种体验能缓解父母是吞噬一切猛兽的早期幻想。如果没有这种体验——而在一个贬低一切权威形式的社会里常常是没有体验的——虐待狂般的超自我则能以自我理想为代价得以发展,而毁灭性的超自我能以那个我们称为良心的、严厉而又关切的内心声音为代价得以发展。
(10) 诺曼·梅勒(1923—〓),美国作家。二战时在太平洋战区服役。他以这段生活为依据于1948年创作了《裸者与死者》,该书已成为美国最负盛名的争议作品之一。后期作品有《鹿园》(1955)、《美国梦》(1965)、《为何我们在越南》(1967)以及一本诗集《女性之死》(1962)等。梅勒是美国当今著名的坦率而不守清规者、美国文学及政治的犀利评论家。——译者
(11) 海茵茨·科赫特认为,有益的、创造性的工作使个人面临着“悬而未决的智力与美学问题”,从而使自恋者从事自我之外的活动。这种工作给自恋者提供了超越自己困境的最好机会。“许多人的经验中多少有点创造性的潜力——无论它的范围是多么狭小。可以通过通常的自我观察与移情作用来认识创造性行为的自恋性质(即创造性兴趣的客体被注入了自恋性质的里比多)。”
(12) 库内特·冯内古特(1922—2007),美国小说家、剧评家。他对世界的荒诞性进行了讽刺性和喜剧性的想象,这主要表现在他的第一部剧本《旺达·生日快乐》(1970)中。他的小说和剧本有《猫的摇篮》(1963)、《第五号屠场》(1969)、《冠军的早餐》(1973)和《滑稽剧》(1976)等。——译者
(13) 理查德·桑内特(1943—〓),美国社会学家。纽约人类学协会的创始人与领导者。著有《叛逆城市的家庭》(1972)、《权威》(1980)等。现为美国国际社会学协会成员。——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