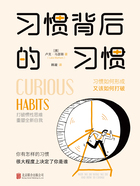
情绪、记忆和行动
还记得2001年9月11日你在哪里吗?如果你现在30岁以上,戴安娜王妃去世那天你记得吗?有些事情会烙印在我们的集体记忆中。
我仍旧记得1996年的美国名人赛 ——格雷格·诺曼(Greg Norman)
——格雷格·诺曼(Greg Norman) 惨败,以及1990年的澳大利亚澳式足球联盟(AFL)总决赛——这仍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一天,历历在目的还有我女儿出生的那一天——排名不分先后,亲爱的克洛伊(Chloe)。我也不会忘记1979年的电影《天涯赤子心》(The Champ)。当瑞奇·施罗德(Ricky Schroder)的父亲在拳击赛后去世时,9岁的我泣不成声。这些事件都因为引发了强烈的情绪而不可磨灭地被铭刻在我的大脑中。
惨败,以及1990年的澳大利亚澳式足球联盟(AFL)总决赛——这仍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一天,历历在目的还有我女儿出生的那一天——排名不分先后,亲爱的克洛伊(Chloe)。我也不会忘记1979年的电影《天涯赤子心》(The Champ)。当瑞奇·施罗德(Ricky Schroder)的父亲在拳击赛后去世时,9岁的我泣不成声。这些事件都因为引发了强烈的情绪而不可磨灭地被铭刻在我的大脑中。
我们具备一整套大脑网络来帮助记忆的形成。海马体是形成记忆的脑区,它所处的位置就在杏仁核的隔壁,而杏仁核则是恐惧(或情绪)中心。
与“9·11”事件相关的恐惧使我的杏仁核过度运转,促使海马体也活跃了起来,那一天所有的事情都历历可数地被记录了下来。那天也是我妈妈的60岁大寿,当时我正用电脑为她剪辑视频,我姐姐打电话来让我看新闻。在电视中看到飞机撞击双子塔是非常可怕的。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很多频道都在重播这个新闻,让人记忆更加深刻。我可能记不住妈妈其他的生日了,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她60岁大寿的那一天。作为一个现年75岁的老者,我的妈妈曾在孙女“丛林”主题的生日派对上扮成大猩猩。她就是这样一个妈妈。这也是一个我会永远记在心里的派对。
在形成记忆方面,情绪的作用是强大的。它帮助我们记住所有背景信息:我们在哪儿,和谁在一起。而决定记忆的首要因素是该事件与正常事件的差异性,以及我们对它的感受。
最终,我们创造了有关事件的故事——这些故事成了记忆。其实,我们并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事实,我们记住的是我们不断重播的有关事件的那个故事。正如在接下来的章节你将看到的,有时候这些故事并不可信(但是它们可以被改变)。
近一百年前,戴尔·卡耐基(Dale Carnegie)注意到一些时至今日仍旧正确的事情:“当与人打交道的时候,记住你面对的不是一个逻辑生物,而是一个情绪生物。”20世纪,很多事情已经发生变化,但是藏在众多奇怪习惯背后的仍旧是情绪。情绪激发旧大脑开展行动。
想象一下,如果你的身体是一辆汽车,那么旧大脑就是驾驶员,它非常努力地躲避其他车辆、坑洞和柔软的边界(你的情绪)。它飞速运转,对每一个向它袭来的情绪做出反应。而你的新大脑在副驾驶的位置手握地图(还记得地图是什么吗?)。旧大脑没有GPS导航——它很老派,喜欢纵观全局的视角。为了让旧大脑朝向正确的方向,新大脑必须给出处于海鞘模式下的旧大脑能理解的内容,指示旧大脑开往正确的方向。新大脑还得负责解释清楚旧大脑的快速决定,通常新大脑并不承认情绪是驱动力——因为面对情绪试图传达的残酷真相可能会创造更大的痛苦。
你有没有对自己说过:“我究竟为什么要干这种事?”想必我们都曾有过。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是根据情绪以及旧大脑出于习惯的条件反射而做决定的。然后新大脑会加入,编造一个故事来将我们所做的行为合理化。
当压力过大的路怒症患者的旧大脑开始运作时,在他反应过来之前他可能就开始竖中指,挑衅不小心插队的老人了。他的旧大脑会绕过所有对情绪信号该有的好奇心,直接臆断老人不该开车。
奇怪的习惯包含感受、想法以及行为,所以理解表层之下的情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觉察到自己的想法才有机会解释或改变自身行为。正如哈佛大学心理学家苏珊·戴维(SusanDavid)博士所说:“通过将情绪看成一个路标,对我们的感受以及原因保持好奇,我们就可以采取更为有意识的行为,而不是任由旧大脑说了算,或者在事后试图用逻辑将行动合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