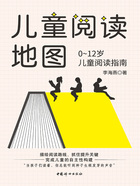
安静凝神
梁启超在《三十自述》[33]中提及幼时的读书经历:
四五岁,就王父及母膝下授四子书、《诗经》,夜则就睡王父榻。日与言古豪杰哲人嘉言懿行,而尤喜举亡宋、亡明国难之事,津津道之。六岁后,就父读,受中国略史,五经卒业。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十二岁,应试学院,补博士弟子员。日治帖括,虽心不慊之,然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更有所谓学也,辄埋头钻研,顾颇喜词章,王父、父、母时授以唐人诗,嗜之过于八股。家贫无书可读,惟有《史记》一,《纲鉴易知录》一,王父、父日以课之,故至今《史记》之文能成诵八九。父执有爱其慧者,赠以《汉书》一,姚氏《古文辞类纂》一,则大喜,读之卒业矣。
静心读书,别有兴味,读书的种子早早地萌芽,梁启超少年有异才,也遇到了好的引路人。这对于多数的孩子来说,殊为不易。儿童的天性是爱嬉笑打闹的,正因为儿童“动”得多,自由开放,不拘一格,到了入学的岁数,得恭恭敬敬地坐下来读书,向着“静”养成谦谦君子之风。
明代的吕得胜、吕坤父子都对蒙学教育颇有心得。当时民间流传一些儿歌,如《盘脚盘》《东屋点灯西屋明》之类,吕得胜认为“夫蒙以养正,有知识时,便是养正时也”,这些儿歌对儿童固然无害,但对品德修养没有什么好处。于是他编写出新的儿歌,“使童子乐闻而易晓焉”。比如吕得胜《小儿语》教育儿童不能急躁慌张,要做到从容和耐心:
一切言动,都要安详,十差九错,只为慌张。沉静立身,从容说话,不要轻薄,惹人笑骂……先学耐烦,快休使气,性躁心粗,一生不济。
也阐述与人说话要温和,被人说了不要恼:
当面说人,话休峻厉,谁是你儿,受你闲气?……与人讲话,看人面色,意不相投,不须强说……当面证人,惹祸最大,是与不是,尽他说罢。[34]
《读书作文谱》中提及“敬”与“静”,可以说点到了成人对儿童期盼的关键处:
涉世处事,“敬”字工夫居多;读书穷理,“静”字工夫最要。然涉世处事,亦不可不静,读书穷理,亦不可不敬。二者原未尝可离……心非静不能明,性非静不能养,静之为功大矣哉!灯动则不能照物,水动则不能鉴物,静则万物毕见矣。惟心亦然,动则万理皆昏,静则万理皆彻。[35]
《千字文》问世之后,被公认为一本好的蒙养教材。从南北朝开始,到隋流行,盛行于唐代,经过宋元明清,为我国蒙学所通用。其流传之广,时间跨度之大,影响之深,可以说是蒙养教材之冠。《千字文》被许多大书法家写成字帖流传至今,如智永、欧阳询、怀素、赵佶、赵孟頫、文徵明、刘石巷。如《千字文》所写,“性静情逸,心动神疲”,心性平和则内心舒适,心气浮动则精神疲惫。无论是涉世处事还是读书穷理,都既需要“敬”,也需要“静”,两者合而为一,相辅相成,心怀敬畏,静气凝神,则可以看到世间万物,洞彻世间至理。
《童蒙须知》篇幅虽小,但规定极为细致,如“凡盥面,必以巾帨遮护衣领,卷束两袖,勿令有所湿”“凡为人弟子,须是常低声下气,语言详缓,不可高言喧闹,浮言戏笑”“长上检责,或有过误,不可便自分解,姑且隐默。又却徐徐细意条陈”“凡子弟,须要早起晏眠”“凡饮食有则食之,无则不可思索。但粥饭充饥,不可阙”等,对于儿童周身洁净、静默隐忍、敬重长上的主张进行了集中的阐释与表达。崔学古《幼训》则提出,“不禀亲命,打骂家人”“骂乳母及老仆”“擒拍蝴蝶、蜻蜓诸虫,践踏虫蚁,折花枝,作顽”“置袜履下衣在案上,置冠帽在椅座床边”“秽手翻动经卷”“讲闲话”“翻弄人书籍文具”[36]等都是不可以做的。
这些修身立德、为人处世之道,可谓用心良苦,何止是儿童需要勉力进取的方向,也是让成年人自律的训话和垂戒。师长希望造就老成练达、秉节持重的儿童,而不是札手舞脚、心浮气躁的儿童,在“动”与“静”之间偏向于“静”的一面。在生活中,要注意穿着,“显出一种老成持重的神气来”[37],在私塾里,不嬉戏,不言笑,喜静怕动成为对儿童的期盼和评判标准。“生而凝重”“如成人”常常被用来形容还处于幼年的孩子。如董仲永,“幼而端谨,不为儿嬉事,便若成人。父母待之不与诸子等,特所钟爱”;叶份“幼修谨,不好弄。居父母丧,哀毁如成人。金紫公爱特异,尝抚之曰:‘大吾门其此儿乎?’及长,种学绩文,遇事穷核根源,不为口耳学”[38]。
遵循规律,明晰何时“静”、何时“动”,为孩子们营造亦动亦静、动静结合的成长环境,帮助他们走向自主和自我驱动,走向动静相宜,是一件非常紧要和必要的事情,也是一个日益增进的生命历程。但倘若受他人驱使,长期熏染在禁锢的环境中,不重视儿童的体育运动,不注重儿童的成长天性,儿童难免失了灵动、活泼、生气勃勃,如果儿童因此失却自主,那就非常糟糕了。儿童的成长得动静相融,才能既有健康的体魄,又有发达的头脑,既能够沉潜蓄势,也能够相时而动。成人须得有足够的耐心、温暖的陪伴和得失之间的智慧。